建于抗日戰爭時期的一批碉堡、炮樓重回公眾視野,它們匿于秭歸深山中已大半個世紀。此前,秭歸的文史普查人員在田野調查時發現并找到了它們。
這些工事是宜昌淪陷后國民黨軍隊為堵截日軍進軍川東而修筑。它們沿著九畹溪河谷兩岸的山坡布防,易守難攻,死死地扼守著日軍進川的陸路通道。大半個世紀的歲月讓它們失卻了當初冷硬鋒芒,布滿綠苔,隱于荊棘叢中。
二戰勝利65周年之際,發現這些抗日工事的秭歸九畹溪鎮有意把這些工事納入當地旅游規劃之中,也讓人們記住那段民族危亡的歷史。

8月10日午后,一天中天氣醉熱的時候。秭歸九畹溪鎮仙女村支部書記王明山和鎮文化干事江勇走在山道上,汗流浹背。
從一條主公路上下來,數百米外的一個山崖叫獅子背,那里有一個炮樓。
走到跟前一股惡臭襲來。進入碉堡的洞口一股糞水流出。“一戶人家把牛拴在里面,冬暖夏涼的。”王明山說,沒作牛圈前,村民常在里面納涼,“一個蚊子都沒有”。
炮樓是在一個突出的巖體上開鑿出來的,貌似一個山洞,4個平方左右。巖體的正上方鑿出一尺許的方洞,可以窺探河谷里的動向。“當初洞口是用來架機槍的。”江勇說,此前的田野調查里,有老輩人描述說,曾看到從洞口伸出來粗黑的機槍管,“很嚇人”。
捏著鼻子走進炮樓內,踮著腳才能避過腳下的牛糞。巖壁布滿了苔綠,壁面凹凸不平,那是當初鋼釬在堅硬的巖壁上留下的鑿痕,一道連著一道。用手撫摸,巖壁上冰涼冰涼的,有種濕滑的感覺。從炮樓內沿著槍眼往外窺探,蔥綠的雜樹遮住了視線。這些植被是這兩年長出來的,那個時候,視野好得很,河谷里的動向一清二楚。
村里89歲的老人袁前桂見證了這個炮樓修筑過程。當初的施工隊就住在他的家里。“一班12個人,他們天天在那里敲啊,砸啊。”
“他們在我家開伙,吃得比我們好。”在袁前桂老人的記憶里,這些兵除了能吃上白米飯外,偶爾還向村民買雞子殺著吃。令老人印象深刻的還有那些軍官的太太們,“她們衣著光鮮在村子里招搖過市。”
當時,在仙女坪村還有一個軍隊衛生所。戰事緊的時候,不斷有傷員從前線撤下來,到這里救治。“很多戰士死了后就埋在醫院旁。”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士兵尸骨文革前被村民刨了。
碉堡群未經戰火洗禮
在九畹溪仙女坪村像這樣處在山崖上的碉堡、炮樓還有4處。它們藏匿在深山之中,逐漸被世人淡忘。去年,全國文物普查時,江勇發現了這些殘留在山里的建筑。
事實上,大山深處的秭歸并未遭遇日軍戰火的涂炭。這里緣何有這么多的現代防御工事?他開始檢索資料,實地走訪,尋找這些工事的來龍去脈。走訪中他發現,這些防御工事沿著九畹溪河谷有很多。它們或是從崖壁上開鑿出來,或是用混凝土澆筑,有的是由木料搭建起來。江勇說,它們有的在上個世紀那些瘋狂歲月里遭人為砸毀。后來村民們發現這樣的建筑結實堅固,是拴牲口的好地方,又用作豬圈、牛棚,有的還成為人的臨時居所。當地一戶村民,因為“成份不好”在一個炮樓里生活了十幾年。
89歲的袁前桂并不能憶起獅子背炮樓的準確時間。“這可能是修得較早的一個炮樓。”根據江勇的考證,這個炮樓修于1938年。
是年6月,日軍攻占安慶,武漢會戰開始。此后經過長達4個多月艱苦卓絕的戰斗,武漢淪陷,中國軍隊撤出武漢。湖北省政府遷宜昌,后遷恩施。1940年,宜昌淪陷后,陪都重慶愈加吃緊。為了能夠阻止日軍鐵蹄西進,中國軍隊加強在長江上的布防。
除加強江防外,國民政府還在陸路加強布防。九畹溪鎮位于長江牛肝馬肺峽南岸,南接長陽賀家坪,是進入恩施、川東的要道之一。江勇走訪調查發現,這些碉堡沿著九畹溪河谷兩岸的山坡布防,易守難攻,死死地扼守著日軍進川的陸路通道。
但這些固若金湯的設施并未經戰火的洗禮。“只有飛機飛過這里,偶爾丟下幾枚炸彈。”日軍的西進鐵蹄被中國軍隊死死地鉗制在宜昌以東。后來的石牌一戰徹底阻斷了日軍西進的步伐,捍衛了陪都重慶,粉碎了日本滅亡中國的美夢。
地下指揮所被后人所砸
沿香溪河谷上溯2公里,江勇帶著記者氣喘吁吁地爬上了一個山坡。這里小地名叫墓林包,海拔708米。當初是一個埋死人的亂墳包,所以得名。二戰期間,中國軍隊看中了這里,一個地下指揮所就建在這里。
這個歷經66年風雨的指揮所呈現在記者面前時已是一個大坑,銅墻鐵壁般的頂蓋已被掀去。這剛好看清這個不到10個平方小指揮所的設計匠心。
圓坑的四壁光溜溜的,厚重堅實。坑壁上有一排整齊的凹臺,是用來放彈匣的。正對著河谷的坑壁上有三個方口。墓林包位于九畹溪、楊林河、西溝河交匯處,視野十分開闊。這三個方口射出去火力如果交織成網,飛鳥都很難逃出這個河口。從地面進入坑內是一個彎曲狹窄的過道,從10多米外慢慢延伸進來。坑壁上有一個孔,指揮所內的人對進來的人一覽無遺。江勇說,指揮所設計上十分有匠心。地下指揮所的透氣口是個煙囪狀的管狀東西,設計者將其設計成彎彎曲曲狀。“你丟個炸彈也不會掉到室內來。”
“全部用美國進口的‘洋灰’和鋼筋澆筑的,牢實得很。”1943年修筑這個地下工事時黃應春4歲。盡管很小,他對這個指揮所的建設情況印象深刻。“我老大還經常到工地上幫忙,我天天跟在屁股后面玩。”黃應春說,差不多一個連的兵力駐在這里。混凝土的材料全部是戰士從河里背上來的鵝卵石,另外還征調了當地民夫。混凝土內部布滿了12號螺紋鋼。
“石壁這么光滑不是一二次粉刷弄出來的,他們的工藝很好。”黃應春說,修筑時戰士們把一棵大樹砍了,鋸成光滑木板用來支模。工期一直從1943年的10月到1944年的3月結束。所有施工結束后,他們又在指揮所的頂上堆放封土,為了偽裝,在上面還栽了幾棵樹。
這個固若金湯的工事在戰爭中逃過了一劫,卻沒有逃過和平年代群眾的打砸。解放后,群眾除去指揮所上面的封土,把屋頂作為曬谷場。1958年大煉鋼鐵,群眾發現混凝土里的鋼筋。于是錘砸、炸藥炸,屋頂終于被掀去。“群眾實在沒有辦法弄出坑壁里的鋼筋,這才讓它逃過一劫。”
在文物普查后,九畹溪鎮的碉堡群已上報給了文物部門。“這里正好在九畹溪景區里,政府想把它納入到景區規劃里。”江勇說,如果有錢,把這些工事修復起來,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也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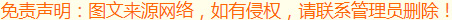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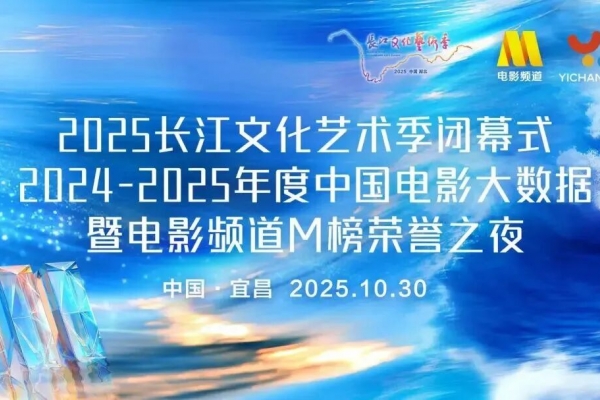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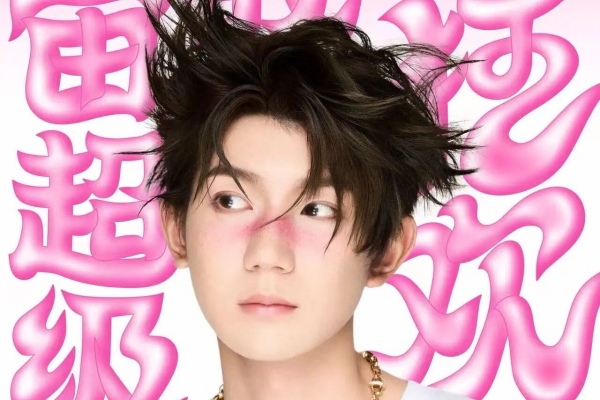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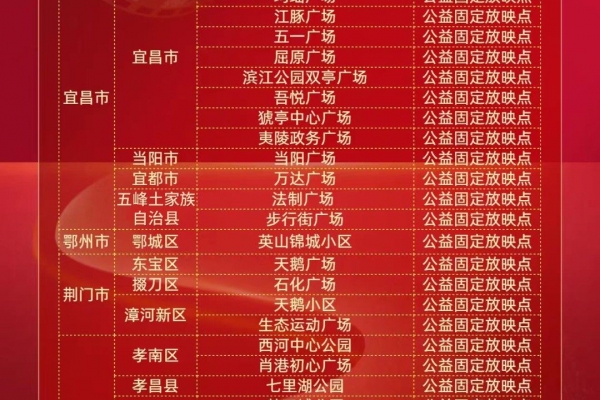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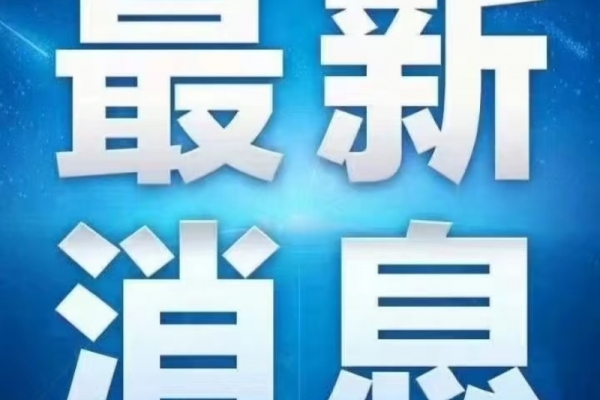










 鄂公網安備 42050302000233號
鄂公網安備 42050302000233號